硅谷之謎與中國鏡鑒:小而巧的起跑
“你們產品這么多,哪個是自己的創新?”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104case.com/article/98738.htm“None。”不料,對方哈哈大笑,一點不難為情。
“原來是個代工公司。”訪客竊竊私語。不過葛濱提醒,這實是求圓半徑的題解之一。
也就是說,從研發、生產制造到市場營銷,清晰的產業分工和社會協作保證了硅谷速度和諸多成本的節約,即以最快時間、最低成本完成“從技術發明到產品,從產品到商品”至關重要的兩個飛躍。
實際上,這也是Edison課程中硅谷與東部“拉動式創新”的另一區別之處:后者的縱向公司結構決定供應商基本不參與創新,而硅谷橫向競爭促成了零件制造商與產品制造商間的緊密合作,并在過程中發揮各自優勢進行創新,從而產生通過新生態系統的建立使新理念價值不斷增加的“推動型價值鏈結構”,最后從產品創新一路沖向如eBay、Yahoo、Google等的商業模型創新。
但如果說,上述之另一“小而靈活”是很多“外來者”沒有成功拷貝硅谷的原因之一(中國企業文化較傾向“大而全”思路,甚至一個企業內就有自己“小醫院、小社區”),那么靈活而健全的人才培養體系則是該半徑的另一解。
“清華、北大與中關村的融合仍非制度化。”今年年初,作為給中關村出謀劃策、同時也是介入中關村發展歷史最長、最全面的第三方獨立研究機構——長城戰略咨詢的董事長、所長王德祿和顧問趙慕蘭在位于Cupertino區的Cypress酒店,向記者作出了如下感慨:就“企業”、“學校”和“政府”三創新環節而言,中國大學對創新的“孵化”是與硅谷的最大差距所在。
“除斯坦福教師可參與建立創新企業外,還表現在取自社會的師資招聘制度上。”趙說,斯坦福等硅谷高校都有專門“咨詢教授”一職,且數量不少,這些人往往都是社會某個領域的強者,具備豐富實踐經驗,直接受益的就是當地學生。”
“不少人離開幾十年后還能回去完成當年沒完成的博士論文,完了還能拿學位,”王隨后指向斯坦福的學籍管理:“而中國想創業的學生,則必須面對魚和熊掌的問題。”
斯坦福當之無愧是硅谷人才培養體系的核心,截至目前其全球畢業生約1.5萬人,培養的人才領導的企業所創造的總產值卻占到了硅谷經濟一半以上。“不過,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學號稱自己是硅谷大學,斯坦福卻不敢,你知道為什么嗎?”葛濱問。
“這是因為這些年來圣何塞州立大學為硅谷輸出了大量的中、低層技能型人才,而這種持續不斷的輸血也包括硅谷的各社區學校。”換言之,硅谷同樣受益于非常重要的人才結構和層次,但求解至此,仍有一些解答因關乎硅谷深層的文化基因而顯得復雜、難以輕易轉化。
比方說,硅谷工程師經常離開公司去實踐不被公司接受的想法、永不怕失敗、專業團體勝過公司間壁壘等;又如,這里風險投資家更青睞奇思妙想而不是具體計劃,因為此地最賺錢的往往是這類早期投資,但這背后又與美國政府對風險投資的立法、規范和對風險資本的權益保障乃至整個社會的誠信機制及價值觀密切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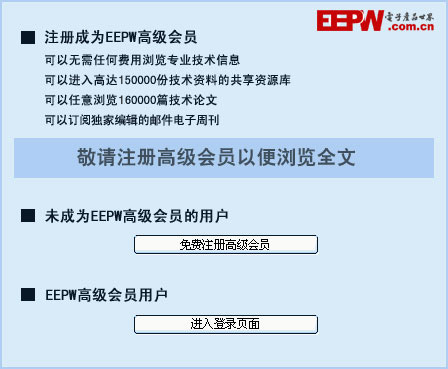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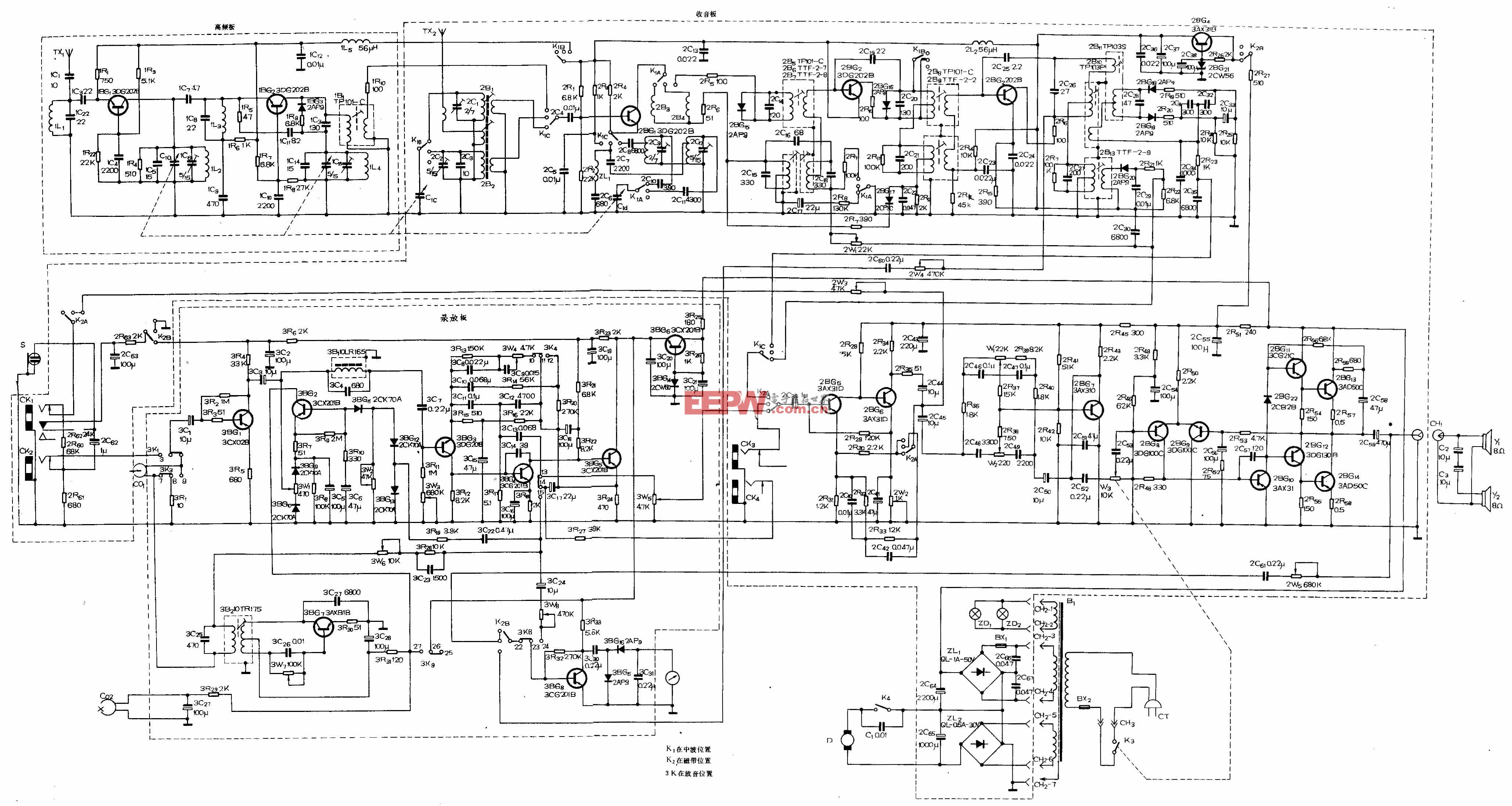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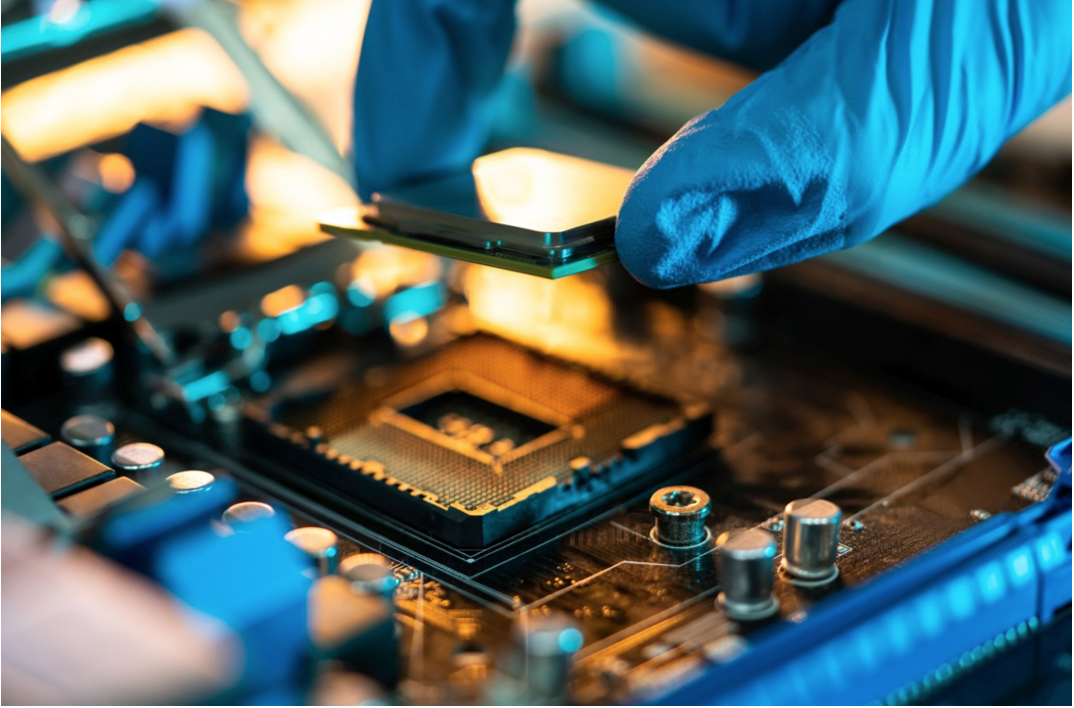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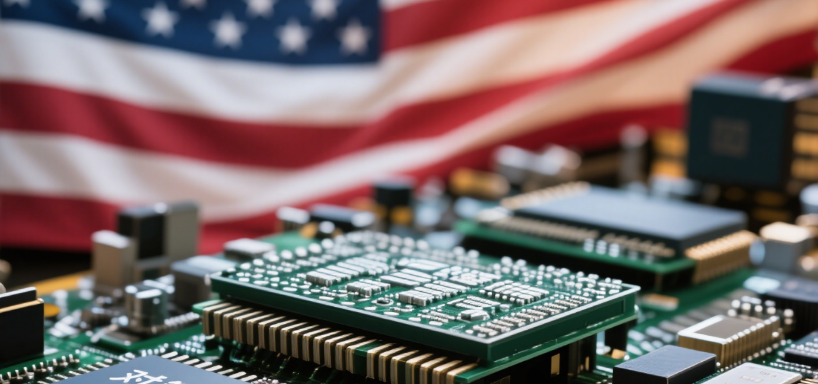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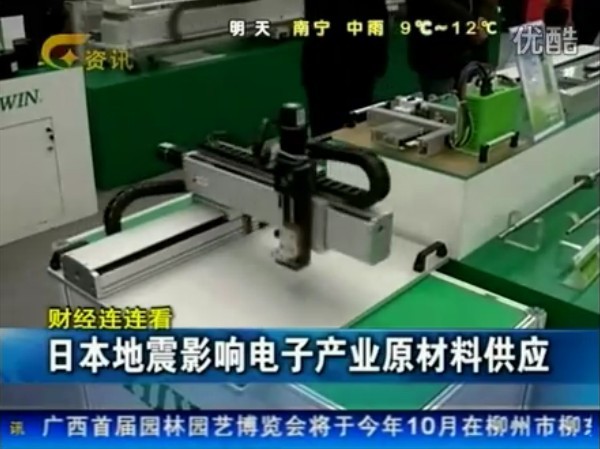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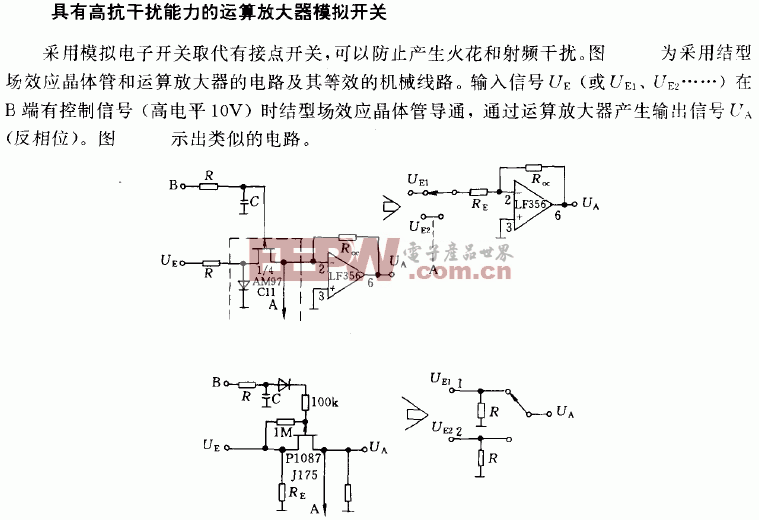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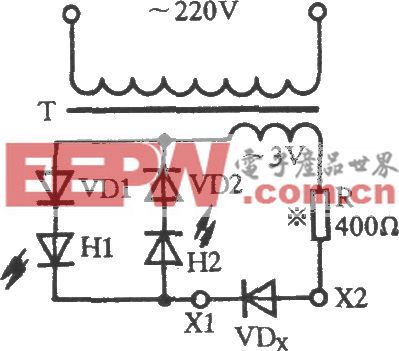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