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專家:機器人與人類是伙伴 中國落后美國5年
以下為馬爾科夫對于人工智能的觀點匯總: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104case.com/article/201601/286077.htm

一、人工智能未來大趨勢
1、人機交互,機器的終極智慧
從“問答機器人”(FAQbots)到 Google Now 和蘋果的 Siri,再到電影《她》(Her),我們看到了斯嘉麗·約翰遜所扮演的人工智能,它能同時進行數百個人類級別的對話。GoogleNow和Siri呈現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人機交互風格:Siri 正在有目的性地模仿人類,并取得了一定成功,具備了一種略顯“別扭”的幽默感;而 Google Now 則選擇充當純粹的信息數據庫,去除了個性或人性。
2、無人駕駛汽車,將人類排除在外
谷歌最初的自動駕駛項目需要兩位專業司機,每個人都有一份類似飛機駕駛清單的文件。坐在駕駛員座位上的人需要時刻保持警惕,并準備好在發生異常情況的時候采取行動。可一些谷歌員工在回家路上,在一整天的工作后有一個令人不安的習慣:他們容易心煩意亂、受到干擾,甚至還可能在車上睡著!
這也被稱為“放手”問題。這里的挑戰在于,需要尋找一種方式,讓那些被其他事情分心,讀郵件、看電影甚至睡覺的駕駛員快速回到緊急情況發生時必需的“態勢感知”(situational awareness)級別。當然,在他們已經逐漸信任的無人駕駛汽車上打瞌睡是很自然的。這是汽車行業 2014 年在堵車輔助系統中需要解決的情況。司機必須讓一只手留在方向盤上,中間可以有 10 秒鐘的間隙。如果司機沒有滿足這個條件,系統就會發出聲音警告,從而脫離自動駕駛模式。不過很多時候,緊急情況可能會在不到一秒的時間內發生。雖然在遙遠的未來,這一問題或許可以得到解決,但以目前的技術卻是無法做到的。
一些汽車制造商已經開始著手處理司機分心的問題了。雷克薩斯和奔馳已經實現了類似的商業化技術,能夠通過監測駕駛員的眼睛和頭部的位置來確定他們是否昏昏欲睡,或是走神。2014 年,奧迪開始研發新系統,用兩臺攝像機來檢測司機是否精力不集中,如果是,那么系統就會突然終止。
但就目前而言,谷歌似乎已經改變了策略,并開始著手解決另一個更為簡單的問題。2014 年 5 月,在向記者介紹了無人駕駛汽車項目的樂觀進展后,他們轉而著手探索一個全新的、受限制的卻也更激進的城市環境下自動駕駛汽車的解決方案。既然無法解決人類分心的問題,谷歌的工程師決定:將人類完全排除在駕駛過程之外。
3、軟件助手,數字化生存之道
20世紀 90 年代初,盡管正處于人工智能的冬天,斯坦福研究所仍然是一個蓬勃發展的商業、軍事和學術人工智能研究的樞紐。Shakey 問世幾十年以后, 機器人仍在大廳里游蕩。當Siri 聯合創始人亞當·奇耶奇耶來到實驗室時,他接手了一個由韓國政府運營的韓國電信實驗室的小型研究項目。項目資金旨在用于開發可在辦公室環境中使用的觸控筆和語音控制系統。“給我們做一個出來。”他們這樣要求奇耶。
為了方便以后便捷地加入其他功能,奇耶決定建立一個系統。這個系統被命名為“Open Agent Architecture”(開放式助手架構)。它被設計用來協助構想出的“委派計算”(delegated computing)。舉個例子,如果計算機需要回答“鮑勃的電子郵件地址是什么”之類的問題,系統可以用很多方式找出答案。奇耶創建了一種語言,使虛擬軟件助手能夠翻譯任務并高效地尋找答案。
奇耶發現自己正處在一場 AI 圈和 IA 圈之間辯論的中心地帶。一方相信,用戶需要完全被計算機控制,而另一方則預見到,軟件助手將在計算機網絡中“生活”, 并代表人類用戶執行任務。從一開始,奇耶就對人機關系有著一種微妙的認識。他認為,人類有時想直接控制系統,然而更多的時候,他們只是希望系統替他們完成某些事,并且不希望被細節騷擾。為此,他的語言把用戶希望系統做“什么”,從任務 “如何”完成中分離了出來。軟件虛擬機器人、軟件助手,既要充當人類的伙伴,也要充當人類的奴隸。
Siri 是未來人類與機器合作的一個優雅、樸素的模型。
4、虛擬機器人,更自由、更放松的人機交互
對話系統正在逐漸進入我們的日常交互。不可避免的是,這種伙伴關系并不總會發展成我們所期待的狀態。
2013 年秋天,電影《她》(Her)轟動一時,講述了由杰昆·菲尼克斯 (Joaquin Phoenix)扮演的男主人公,與斯嘉麗·約翰遜配音的虛擬助手相愛的故事。《她》是一部科幻電影,故事發生在南加州未來的某個時間,一位孤獨的男性與操作系統墜入愛河。許多觀看了這部電影的人似乎都完全能夠接受
這種結局。截至2013 年,全球已經有數百人擁有了多年使用蘋果 Siri 的經驗, 這越來越讓人感覺到“虛擬助手”正從新奇走向主流。
電影《她》也講述了一些“奇點”的概念,即機器智能在某個點上會加速, 最終超越人類智能成為獨立的存在,并將人類拋在身后。《她》以及同年夏天上映的另外一部癡迷于奇點的科學電影《超驗駭客》(Transcendence),它們的有趣之處在于——它們描繪人機關系的方式。
在《超驗駭客》一片中,人機交互從愉快變成了黑暗,最終,一臺超級智能機器摧毀了人類文明。在電影《她》中,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因為計算機智能發展過于迅速,人類和他的操作系統之間的關系發生瓦解。由于不愿意接受 1 000 種同時進行的關系,計算機超越了人性,并最終選擇離開。
也許,與機器人交互的那種自由、放松之感,正是因為在連線的另一邊并不是一個令人難以捉摸的人類。也許,這根本與人際關系無關,更多的在于是取得控制成為主人還是成為奴隸。
無論支撐這些交互的心理因素究竟是什么,總之它已經讓卡珀有些錯愕。卡珀所看到的人類的心理維度,遠比之前預料的要多得多。所以,雖然在偶然間發現了這一新興業務,但她卻打起了退堂鼓,并在 2014 年關閉了“我的完美女友”。她認為,肯定存在一種更好的商業形式。事實證明,卡珀的這種商業第六感來得正是時候。蘋果向 Siri 張開懷抱,就此改變了虛擬助理市場。在計算機的世界里,理解對話系統不再是什么古怪的創新,而是一種逐漸成為主流的交互方式。
5、救援機器人,進入極端環境作業
由于美國政府要求提供人道主義援助,DARPA 也自然而然地參與了這場核危機之中。(“9 · 11”事件后,該機構曾派機器人前往遭受襲擊的世貿中心搜尋幸存者。)DARPA 的官員們開始協調福島事件的應對工作,并聯系了美國多家曾為三里島、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提供過援助的公司。美國向日本派遣了一小批機器人隊伍,希望進入核電站完成維修工作。可惜,當核電站人員接受機器人使用培訓的時候,避免最嚴重破壞的最佳時機已悄然逝去。這一點尤其令人感到沮喪,因為如果能夠迅速部署機器人,那一定會帶來不小的轉機,并能有效控制破壞程度。“最終,機器人所能帶來的最大幫助是對已生的大面積損毀進行調查,并獲取輻射數據。能夠減輕災害等級、進行早期干預的黃金時期早已逝去。”
6、從AI(人工智能)到 IA (智能增強),人機共生才能重塑新世界
我探索了科學家、工程師和黑客們研究的“如何深化人與計算機間的聯系”這一問題。在一些案例中我發現,設計師們堅持認為人工智能和“智能增強”(intelligenceaugmentation,IA)之間存在互相矛盾的關系。通常, 這最后會被歸結為簡單的經濟學問題。現在,對這種性能遠超 50 年前早期工業機器人的新機器人的需求正在不斷上升,甚至在一些早已高度自動化的行業, 比如農業中,一大批新型“農業機器人”正在駕駛拖拉機或收割機作業,從空中監管并提高農業生產率。本書的主題是辯證地看待這些設計者的工作。他們制造出的系統既可以讓人類變得更強大,也有可能取代人類。安迪·魯賓(Andy Rubin)和湯姆·格魯伯(Tom Gruber)的理論就體現出了最清晰的對比。魯賓是谷歌機器人帝國最初的架構師,格魯伯則是蘋果 Siri 智能助手的主要設計師,他們都是硅谷最優秀、最耀眼的明星,他們的工作都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之上:魯賓模仿了約翰·麥卡錫,格魯伯則追隨了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或取代人類,或讓人類變得更強大。
當 AI 和 IA 圈引領的技術繼續重塑世界時,未來其他的可能性就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在那個世界中,人類和人類創造的機器共同存在,一起繁榮——機器人照顧老年人,汽車自動行駛,重復勞動和辛苦工作都消失了,新的雅典誕生了,人們研究科學, 創作藝術,享受生活。如果信息時代將以這樣的形式發展,那將無比美妙,但它又怎能成為一個預言式的結論呢?同樣,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比起解放人類,這些強大、高效的技術更有可能促進財富的進一步集中,催生大批新型技術性失業,在全球范圍內布下一張無法逃脫的監視網,同時也會帶來新一代的自動化超級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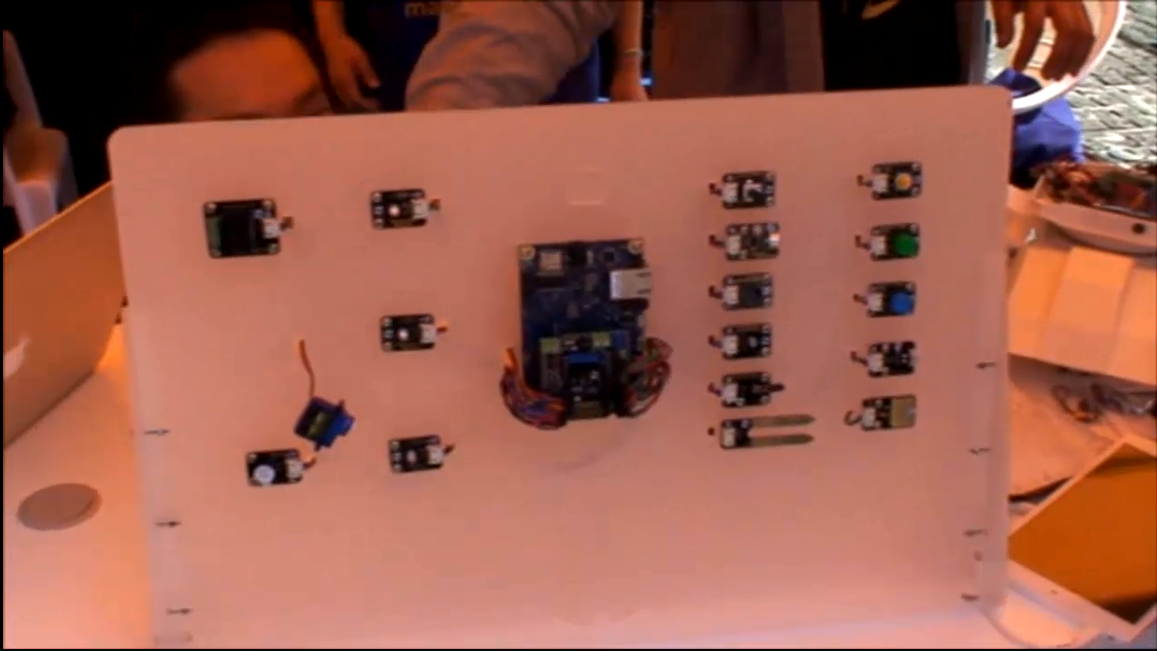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