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qū)留不住大學生凸顯3大原因
10年來,四川省先后選派到村(社區(qū))工作的8600多名大學畢業(yè)生,流失率達70%以上。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劉中伯認為,其中主要有4個原因:工作重視不夠,經(jīng)濟待遇偏低,教育管理工作沒跟上,政治激勵不到位。“人難留,留人難”,問題不容忽視,亟須反思和分析。
社區(qū)基層為何留不住人?究竟是什么讓這些大學生選擇離開?帶著疑問,記者走訪了社區(qū),以及在社區(qū)工作的大學生們。
不溫不火缺乏挑戰(zhàn)
嚴馨,女,在社區(qū)工作時間:8個多月
“來了才知道,社區(qū)要做這么多事。”與之前采訪的每個大學生一樣,嚴馨發(fā)出同樣的感慨。去年8月14日,她到社區(qū)的第一天就傻了眼:勞動保障、計生、低保……大項小項加起來,社區(qū)的工作有160余項之多。之前她與多數(shù)的大學生一樣,以為社區(qū)只是偶爾調解糾紛,其余時間都不會有什么事。
在芳鄰社區(qū)做了8個多月,嚴馨就選擇了離開。并非因為在社區(qū)的工作繁雜,而是她發(fā)現(xiàn)自己并沒能得到一些實打實的技能,反而差點快把自己學了4年的專業(yè)丟掉。
嚴馨剛到社區(qū)就分配到了任務,主要工作是勞動保障:幫下崗工人推薦工作,去商鋪調查有無拖欠員工工資等。而后是人大代表的選舉,作為主任助理,嚴馨主要幫忙發(fā)放選票、張貼通告、統(tǒng)計選民。這些工作在嚴馨看來都很容易,需要的只是耐性。而在技能上,根本學不到什么東西。大學學了4年的知識,一點也沒有用起來,嚴馨認為很不值。“這不是白交了學費嗎?如果干滿2年,我肯定全部都忘完了。”嚴馨甚至不知道社區(qū)有什么事情可以拿出來說。“以后我出來做其他的工作,如果別人問起有什么工作經(jīng)驗,我還真的說不出來。”
更讓嚴馨沮喪的是,很多時候,同學會說她看起來沒有朝氣。嚴馨把這歸結于在社區(qū)工作的結果。她開始考慮離開社區(qū),另外去找工作。正猶豫中,嚴馨在會計班碰上了大學的師姐。“其實在公司上班更鍛煉人,不一定非要在社區(qū)。”師姐的一句話讓她下定了離開的決心。剛好師姐所在的土地整理公司急需招人,嚴馨應聘上了。5月中旬,她向社區(qū)遞交了辭職信。
離開社區(qū)到公司上班,嚴馨發(fā)現(xiàn)自己技能方面的東西還差很多,但卻踏實不少。“現(xiàn)在至少可以知道自己需要學什么,如果呆在社區(qū),就不會知道。”
嚴馨的父親非常支持女兒到社區(qū)工作,想讓她能在基層學會與人的溝通和相處。這一點嚴馨也很贊同,但她認為,8個月的鍛煉已經(jīng)足夠,“社區(qū)的事情不溫不火的,任何人都可以做,沒什么大的挑戰(zhàn),我們年輕人還是應該出去闖一闖的。”
在社區(qū)工作期間,還有一件讓嚴馨頗為郁悶的事。剛到社區(qū)沒多久,嚴馨就如何將團委的工作搞起來,花3天時間寫了一份詳細的計劃書。找社區(qū)拿團員名單時,才發(fā)現(xiàn)社區(qū)里沒有團委。后來,這件事就擱置下來了,“根本就沒有時間。”勞動保障檢查—創(chuàng)佳—人大換屆選舉,社區(qū)工作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很多時候連雙休日都沒有。
工作太累生活窘迫
馬世中,男,在社區(qū)工作時間:2個月
成華區(qū)二仙橋街道辦事處西北路社區(qū),選聘來的大學生馬世中已經(jīng)離開大半年。他只在這里干了2個多月。高高大大、皮膚黝黑,穿著略舊卻洗得干干凈凈的T恤———社區(qū)工作人員蘇培發(fā)還記得這個大男孩第一天來的樣子。
“人很老實,也很能干。幫了我們不少忙,分擔了不少工作。”馬世中來社區(qū)報到的時候,正好遇到再就業(yè)做臺賬,“這么大一疊,他很快就弄好了。”蘇培發(fā)用手比畫著。再就業(yè)要做臺賬,數(shù)量龐大的失業(yè)人員資料需要全部輸入電腦,
在這一方面,馬世中起到了大作用。他和另一個同學一起,包辦了整個街道辦事處的資料錄入。
蘇培發(fā)印象中,馬世中性格溫和,平時也不多話,叫做活的時候,從不推辭。社區(qū)工作人員都很喜歡他。去年11月馬世中離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蘇培發(fā)他們都感覺不習慣,“最大的感覺是少了一個男同胞,少了一個勞力。”“就是,他個子高,掛東西啊什么的都很方便。”旁邊工作人員打趣道。
馬世中的離開,有些出乎蘇培發(fā)的意料。但事后回想起來,卻也是必然之事:初衷很好,但擺在面前的是生活的現(xiàn)實。
馬世中的運氣不好,來的時候正是社區(qū)最忙時。2個多月來,經(jīng)常加班到深夜。“搞這個社區(qū)的事情太累了,都是一些婆婆媽媽的事。”他曾這樣對主任段勝華說。事實上,社區(qū)的工作人員都知道,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更多的是因為生活上的窘迫。
馬世中是東北農村人,畢業(yè)于成都理工大學。他在學校附近十里店租了個單間住,每月800元的補貼,令他的生活捉襟見肘。蘇培發(fā)替他粗算了一筆賬,他每個月在吃住方面就需要650元,基本沒有什么結余。蘇培華把自行車借給了馬世中,不然,這個大小伙子只能每天走很遠的路上班。
短短2個月的時間,馬世中主要做再就業(yè)的工作。蘇培發(fā)說,沒遇到入戶調查,還算馬世中運氣。“我們這里是成華區(qū)最偏遠最窮的地方。”西北路社區(qū)的路很爛,晴天全是灰塵,雨天全是泥漿,要挨家挨戶上門調查,確實很難,也很遠。西北路社區(qū)2000多戶6000多人,人數(shù)不多,卻分散在1.1平方公里的范圍,而有的街道才管零點幾個平方公里。“所以說社區(qū)確實很鍛煉人。”
馬世中沒有堅持下來,蘇培發(fā)和其他社區(qū)工作人員在惋惜的同時也表示理解:一個剛畢業(yè)的大小伙子,血氣方剛,來做這種瑣碎又磨人心志的事情,肯定會不習慣。“就算真的干滿2年,他多半也不會留下來,而且工資確實有點低,他的基本生活都成問題,很多時候還靠女朋友的接濟。”蘇培發(fā)還記得,馬世中有一次穿了一雙新的運動鞋,大家都猜肯定是幾百塊錢的名牌。問了以后才知道,這雙鞋子僅值20塊錢,還是他下了很大決心才買的。
正因為如此,馬世中離開時,社區(qū)的工作人員沒有過多追問。他們只是開了一個歡送會,大家一起吃了一頓飯。
聲音 我們就是試驗品
社區(qū)留不住人,除了一些大學生自身的原因,政策的延續(xù)性也是一大焦點:2年服務期滿后怎么辦?從各地反饋的情況來看,一些地方的大學生到農村、社區(qū)后留不住,人留住了心也留不住。較早開展“大學生村干部”計劃的海南儋州、江蘇阜寧等地,由于在待遇、政策落實等方面的原因,當年的“大學生村干部”目前基本上已經(jīng)流失。
針對大學生的流失,四川省今年同步出臺了9項激勵保障措施。省委組織部相關人士介紹,此次選聘到村(社區(qū))任職的大學生干部,補貼待遇與“三支一扶”、“西部計劃”等志愿者相比,有所提高。具體為:研究生每月補助1500元、本科生每月補助1100元、專科生每月補助900元(民族地區(qū)分別增加200元)。任職1年且考核合格的,每人每年增發(fā)不低于1000元的一次性生活補助。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參照鄉(xiāng)鎮(zhèn)(街道)事業(yè)單位干部標準執(zhí)行。
而此次“一村(社區(qū))一名大學生干部”計劃,針對服務期滿的大學生在考錄省內公務員時也給出了相當優(yōu)惠的政策,符合條件的還可納入選調生范圍。但一些大學生認為,這些政策的可操作性仍值得商議,比如考公務員的優(yōu)惠政策,怎么個優(yōu)惠法?
“這個現(xiàn)在還處在一個摸索的階段,我們其實都是試驗品。”坐在社區(qū)辦公室,李婷笑著說。
分析 得不到尊重是最大原因
“三個原因,壓力大,收入低,得不到尊重信任。”雙林中橫路社區(qū)主任付瑜康說出大學生離開的原因,斬釘截鐵。“得不到尊重是最大的原因。”
去社區(qū)工作的大學生,大部分都是女生,平均年齡在22歲—24歲之間。平時的工作一般能應付,居民也沒有太大意見,但是一旦關系到利益,對這樣的年輕女孩子,居民有時不太信任。
嚴馨有親身體會。當時下崗工人可以申請靈活就業(yè)和社保補貼,這項工作由嚴馨和社區(qū)專職工作人員汪曉燕負責。工人們每個月會來社區(qū)交存折和工作證明的復印件,社區(qū)將這些證明上報,回返。因為關系到錢,居民一般都找汪曉燕,即使人多需要排隊。“他們不信任也沒辦法,反正日久見人心嘛。”嚴馨安慰自己,但是想起來,還是免不了鼻子一酸。比起之前居民的無理取鬧,這樣的不信任對她來說,打擊更大一些。
社區(qū)的環(huán)境,社區(qū)居委會工作人員之間的和睦,都是大學生們考慮的因素,他們認為這很重要。大學生李婷家住望平街,選報社區(qū)時,她在母親的陪同下去了望平社區(qū)和祥和里社區(qū)考察,最后選中后者,“感覺這里很和諧。”
大學生們的去或留,在望平社區(qū)書記陳德全看來,除去這些客觀因素,最終還是得看本人的意愿。據(jù)他了解,去年成華區(qū)招進社區(qū)的98名大學生,是從1000多個報名者中一步步淘汰篩選出來的,競爭相當殘酷。
“他們一來就是800元的工資,我們這里的人都是600多。”陳德全認為,工資上已經(jīng)給予了這些大學生重視。一些地方的大學生中途離開,他多少都有聽說。原因在他看來,一是太累,二是與當?shù)厣鐓^(qū)的不融合。“我們剛開始做這個工作的時候,貼個通知都不好意思,更不用說做大嬸大媽的工作,現(xiàn)在還不是什么都好了。”陳德全笑著說:“關鍵是一個適應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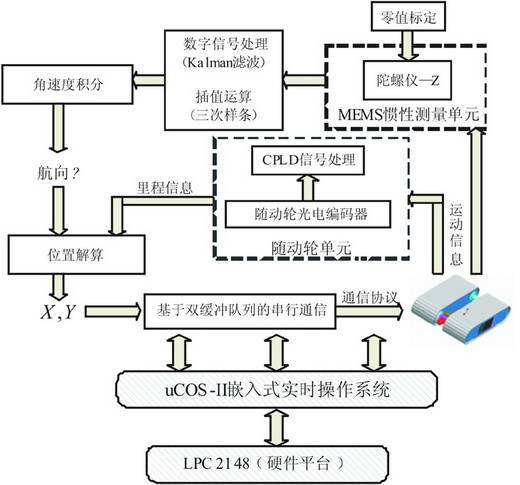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