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個大早, 趕個晚集: 蘋果AI的曲折之路
知名Apple分析師Mark Gurman在外媒發出一篇長文, 題為《Why Apple Still Hasn’t Cracked AI》( 為何Apple仍未攻克人工智能),揭露了Apple內部對AI態度的搖擺,內部的斗爭和難以克服的技術瓶頸。
讓我們把時間倒回1985 年,年輕的喬布斯在接受在一檔電視節目采訪時,就談到了未來對于人工智能的暢想,他表示:“我們也把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輸入進電腦,捕捉亞里士多德的潛在世界觀,還能問亞里士多德問題,并得到答案。”現在看來頗像如今的各種大語言模型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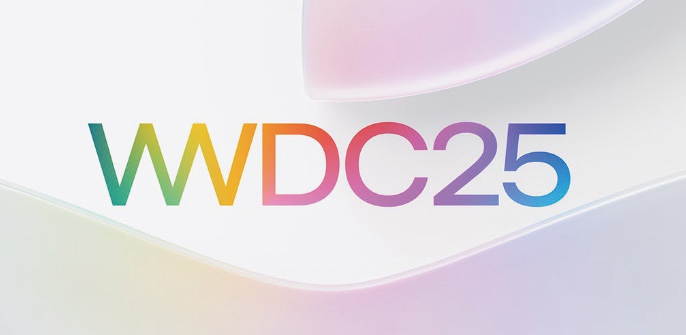
而到了2011年,喬布斯生命的最后時光,Apple推出了Siri,這一智能語音助手在當時堪稱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產品。它能夠理解用戶的語音指令,并執行諸如預訂餐廳、查找電影院等操作,讓人們看到了智能交互的未來。喬布斯對Siri 寄予厚望,認為它遠不止是一款簡單的應用,而是一個能夠改變人們與技術交互方式的重大突破。
Siri的出現,也標志著Apple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早期布局。喬布斯的理念是,Apple應該為用戶提供更優質的、精準挑選的內容,而不是讓用戶被動地去搜索。這一理念深刻影響了Apple的后續發展方向,也讓人們看到了Apple 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潛力。

在當時,Siri的技術領先性讓Apple在智能語音助手領域占據了先發優勢。它不僅能夠識別語音指令,還能通過與互聯網服務的結合,為用戶提供更實用的功能。例如,用戶可以通過Siri 查詢天氣、設置提醒、發送短信等,這些功能在當時都顯得非常先進。喬布斯的遠見在于,他看到了語音助手在移動設備上的巨大潛力,認為它將成為未來人機交互的重要方式之一。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作為如今的Siri,對于Apple來說,其實是一個“撿來的孩子”。為什么Apple 的語音助手會叫“Siri”這么一個似乎毫不相干的名字呢?因為,Siri 來自SRI,也就是斯坦福研究院,他們從DARPA獲得了1.5 億美元的資金,用于開發他們所謂的認知軟件助手。

起初SRI的計劃是與電信公司或手機制造商合作研發“認知軟件助手“但是無人理會,SRI不想放棄這個項目,只能自己獨立完成它。Siri項目最終成為Siri公司,并于2007年成立。三年后,Siri在Apple應用商店首次亮相,而Siri的出現,與喬布斯對于語音助手的想象不謀而合,僅僅上架Apple Store兩周之后,他們接到了史蒂夫?喬布斯本人的電話。到2010年4月,Siri公司接受了Apple的報價,允許這家科技巨頭收購這項技術,并使其成為其軟件陣容的一部分。Apple給出的報價我們現在不得而知,但是種種消息顯示,其價格接近2億美元。
隨著時間的推移,作為“撿來的孩子”的Siri在Apple的發展卻并不順利。盡管Apple在早期收購了一些AI相關的小型公司,如Laserlike、Tuplejump、Turi等,但這些收購并未能有效地推動Apple 在Siri 技術上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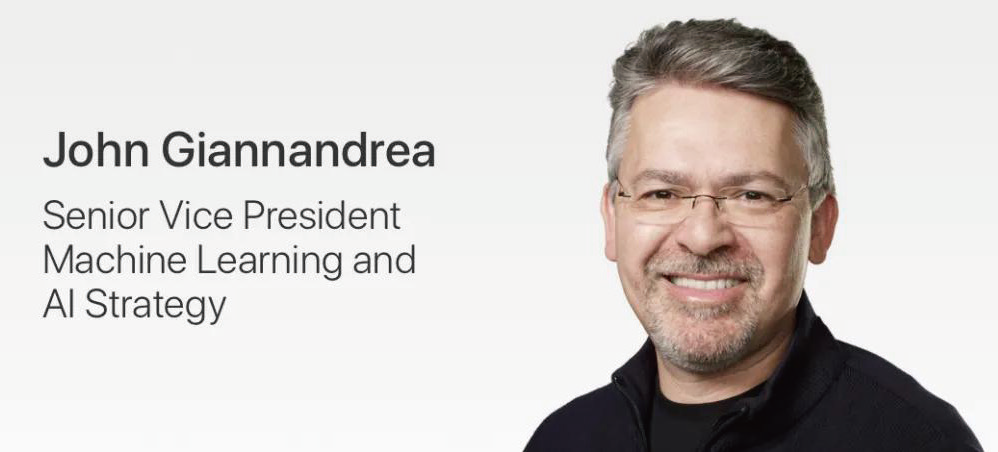
而在AI的應用方向上,Apple也更是顯得有些猶豫不決,未能像在其他領域那樣迅速而堅定地打造出具有革命性的產品。
在Siri面世僅一年后,三星就拿出了自己的競品,而三年之后,亞馬遜的Alexa初試啼聲,又過了兩年,Google Assistant姍姍來遲。隨后就是各類語音助手如雨后春筍般紛至沓來,Apple在AI方向的躊躇,直接導致了Siri更新緩慢,漸漸成了一次Apple 的“起個大早,趕個晚集”。

2018 年,Apple決心變革,從谷歌挖來了約翰?吉安南德雷亞(John Giannandrea)擔任AI 負責人,希望借助他的經驗和影響力推動Apple 在AI 領域的發展。
但是,據Apple 員工的一些內部爆料:吉安南德雷亞是一個好的開發者,但是,他卻很難成為一個好領導者。據Apple 的員工所言,吉安南德雷亞是一個安靜隨和的人,他不喜歡和別人起沖突。他對于機械學習的態度極其佛系,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他常常安慰員工:“機械學習研發得快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像爬上一樣,一步步慢慢往上爬最終一定能取得成功。”員工和知情人士反饋,吉安南德雷亞在Apple 核心圈中難以融入,難以推動變革。他性格低調,未足夠爭取團隊所需資金。一名高管曾透露,吉安南德雷亞的團隊缺乏其他Apple 工程團隊的緊迫感。
雖然,吉安南德雷亞的行事風格很招員工喜歡,但是作為一個“好人”,并不代表能做出好產品。于是,在他的帶領下,AI/ML團隊在公司里獲得了一個AImLess(沒有目標)的雅號。Apple的AI團隊每天的工作就是上班摸魚,下班還是摸魚,再加上吉安南德雷亞的“好人”屬性,晉升和休假都比別的團隊待遇好。
引發了公司內部其他團隊的極度不滿,經常與AI團隊共事的軟件團隊就表示,他們一直以來都在給AI團隊兜底,AI團隊一直在“摸魚”,而且薪資高,假期還多;而AI團隊則表示軟件團隊太“卷”。甚至,軟件團隊為了不讓AI 團隊拖自己后腿,居然在團隊內部又組建了一個“AI部門”。這樣兩個團隊放在一起,怎么能做好產品呢?
然而,Apple還有一個更致命問題——高管對于AI的路線認知也不統一。
最開始,Apple計劃打造兩個模型,分為一大一小,小模型運行在本地,運行一些簡單的指令,同時也能保護用戶的隱私;而大模型就在云端運行,處理一些復雜的任務。沒過多久,Siri 的高層就又決定改用一個模型來解決所有問題,這樣做就必然要用云端大模型,這顯然和Siri團隊最開始堅持的隱私政策背道而馳,直接導致了一些堅持隱私保護的Siri 團隊員工離職。
而這時候,ChatGPT的橫空出世更是打了Apple一個措手不及,更要命的是,AI 團隊的領導“好人”吉安南德雷亞絲毫沒有意識到ChatGPT的革命性,據透露,他曾告訴內部員工:“一個聊天機器人,是不會給用戶帶來多大價值的。”這直接導致了Apple在LLM項目上的遲緩跟進。
當然,Apple在AI上的失敗也不能全賴管理和人事上的問題,Apple在AI技術的研發上也確實面臨著一些更實際的困難。
首先,AI的發展需要大量的數據來進行模型訓練,而Apple一直以來強調用戶隱私保護,對數據的使用有著嚴格的限制。這使得Apple的研究人員在訓練AI模型時,無法充分利用Apple龐大的用戶數據,只能依賴于第三方授權數據集和合成數據,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AI模型的性能和應用范圍。
這一問題在與其他科技巨頭的對比中尤為突出。例如,谷歌、Meta等公司憑借其在搜索引擎、社交媒體等領域的優勢,能夠收集大量的用戶數據,并利用這些數據來訓練和優化其AI模型。而Apple的隱私政策雖然在保護用戶隱私方面贏得了好評,但卻成為了AI 技術發展的桎梏。
其次,Apple在AI硬件資源的采購上也相對保守。與亞馬遜、微軟等競爭對手相比,Apple在GPU等關鍵硬件的采購量較少,導致其AI 模型的訓練速度較慢,進一步拖累了A技術的發展進程。在AI時代,硬件資源的投入對于技術的快速發展至關重要,而Apple的這一保守策略顯然不利于其在AI 領域的競爭。
最后,不僅在硬件上落后,據Apple 及其他公司高管透露,Apple 的AI 員工也數量遠少于競爭對手。對Apple 而言,錯過潛在的顛覆性技術并不致命。
畢竟Apple 常常會讓同行先探索新技術去驗證市場,而后再打磨產品,向用戶推出設計精良、也更易用的版本。這種策略也塑造了用戶對Apple“不求最新,但求最好“的印象。一直以來,Apple 都憑借精心打造的產品、精選內容和每年一次的軟件更新,成為全球最有價值的科技公司。
Apple 也是這么想的,在今年5 月的財報電話會議上,庫克被股東問及AI 延遲的問題時,他表示只是需要更多時間以達到Apple 的質量標準,“沒有太多其他原因,只是比我們預期的時間長了一些。”
但問題是,多長算長呢?在AI 領域,留給Apple的時間可是已經差不多了。
(本文來源于《EEPW》202507)



評論